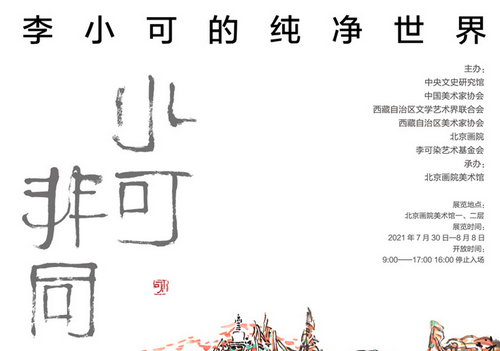|
一代国画大师齐白石(1864——1957),不但艺术成就为世人所叹服,而且其人格魅力也为世人所赞叹。其傲、其痴、其谦堪称三绝。 齐白石傲,傲如古松 在近代,画而优则仕的人屡见不鲜,如张道藩。但白石先生傲骨一身,耻于从俗。先生壮年时曾教夏午贻的妻子学画,夏午贻想好好感谢他,要给他个官做。先生当即画蟹数只并题诗一首:“多足乘潮何处投,草泥乡里合钩留。秋风行出残蒲里,自信无肠一辈羞。”他以甘居草泥乡里的螃蟹自喻,婉言谢绝了夏午贻的美意。先生出身农家,早年靠做木工活维持生计,所以常遭人轻视。有一年他作客胡沁园家中。胡家有位门客丁拔贡擅长制印,先生求他赐印一枚,丁拔贡借口先生的石章磨得不平,再三推辞。先生知道丁拔贡瞧不起自己这个出身寒微的画匠,遂傲然不再复求,回家买了印泥,又捡回石头一担,照着一本借来的《二金蝶堂印谱》,磨了刻,刻了磨,弄得房间里石浆满地,无处落足。而先生没想到,因自己这一傲,最终竟成了治印高手。 齐白石痴,痴如顽石 先生喜欢画螃蟹,也非常喜欢吃螃蟹。一天与家人吃饭,先生忽然停住筷子,敛气凝神地盯着盘中螃蟹,若有所思。夫人见状惊问何故,先生方如梦初醒,一边把蟹腿指给夫人看,一边眉飞色舞地说:“蟹腿扁而鼓,有棱有角,并非常人所想的滚圆,我辈画蟹,当留意。”夫人素知他痴,也懒得去数落,罚他吃一只大螃蟹了事。 先生让弟子侍画于侧,常出其不意地考问:“虾背从第几节弯起”、“螳螂翅上的细筋有多少根”、“牡丹的花蕊和菊花的花蕊有什么区别”。诸如此类怪问题,弄得弟子们往往手足无措,先生却娓娓而谈,如数家珍。 1950年,先生年近九旬,《人民画报》社请先生赐画和平鸽,先生慨然应允,却又迟迟不动笔。关门弟子娄师白问何故,先生说:“我以往只画过斑鸠,没画过鸽子,也没有养过鸽子,不好下笔啊!”后来先生专门买来鸽子放养院中,反复揣摩它的一举一动;又到养有鸽子的弟子家观看鸽子,边看边对身边弟子说:“要记清楚,鸽子的尾巴有十二根羽毛。” 齐白石谦,谦如空谷 同行相轻,是文人的通病。先生虽然誉满华夏,但对前辈画家和同辈画家都非常恭谨,显示了一位大师、一位长者应有的谦逊风范。 先生作画,师古而不拘古意,他主张“下笔要我有我法”,但他对先辈画家的成就却深表景仰,尤其推崇徐渭(号青藤)、朱耷(号雪个)和吴昌硕三人。曾赋诗说:“青藤雪个远凡胎,老缶衰年别有才。我愿九泉为走狗,三家门下轮转来。”也许正因为先生的谦虚,才使他如海纳百川般吸收前人艺术的精华,从而推陈出新。 先生对同时代的画家也尊重有加,他常以一句话来自律:“勿道人之短,勿说己之长,人骂之一笑,人誉之一笑。”正是这种谦逊和宽容,使先生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和艺术上的取长补短。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,某记者造谣说先生看不起徐悲鸿,认为徐悲鸿只不过到国外镀了层金而已。先生得知此事勃然大怒,对人说:“悲鸿是我多年的知己,他画人画马冠绝当世,我佩服之至!” 1936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到北平办画展,先生不顾年事已高,亲往助兴,临走时还买了一幅画,来表达对大千的一片厚意。过了一段时间,有人在先生耳边吹风,说张大千太狂妄了,一点儿也瞧不起先生,自诩“大千可以奴视一切”。先生听后,拈须微微一笑,不置一词。不久先生刻了“我奴视一人”的印,弟子问“一人”指谁,先生说:“我就是奴视造谣说‘大千奴视一切’的这个人。”此语一出,谣言便风息浪止了。 欲立艺者,先立人,这就是齐白石大师留给后来者的有益启示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