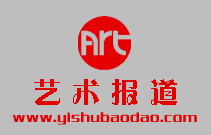|
按:董其昌的南北宗说对明末以来的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尽管时至今日,和四百年前相比,包括中国绘画在内的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,但在变化的深处我们仍然能够发现,有某种稳固的机制在影响着中国文化,也包括中国绘画的形态。南北宗说是否属于那种稳定的内核?如果是,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本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交流。 本期嘉宾简介: 杨惠东: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,《国画家》杂志主编,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,中国美协河山画会秘书长,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。 出版有《石涛山水技法解析、《罗聘》 、《清初四僧绘画》、《蓝瑛》等专著和多种个人画册,发表学术论文多篇。 丁亚雷:画家、艺术评论家、文化学者。南京艺术学院教师、中央美术学院博士。代表作品《武人画》系列。 朱啟辰:收藏家、文化学者。 北宗的“原罪”? ——关于董其昌南北宗论中“崇南贬北"思想的漫谈。 丁亚雷:我是这么想的,一个很有趣的认知现象就是二元结构。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,好像这都是一个方法论的基础。其实中国画后来所谓南北分宗,或许也是一种认知习惯而已。 比如,董的南北宗立论基础和禅宗的南北分宗有关系。禅宗对神秀和慧能的形象刻画,其实多少也能代表点南北宗的各自方向。他们的这种形象和后来董对南北宗的评价有着形象上的直观,而禅宗的南北宗论其实也就是一种认知的二元模式而已。“好坏”正好与之对应。 
李思训 《江帆楼阁图》101.9 x 54.7cm 绢本青绿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杨惠东:诚如亚雷兄所言,所谓的南北分宗无非就是一种认知的二元模式,事实上在董其昌立论之初,仅仅只是指出山水画史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,或许并无崇南贬北之意。在文艺批评中,任何一种经过归纳而上升来的理论皆有其片面之处, 因此,所谓的“崇南贬北”很大程度上,要么是郢书燕解,要么是人云亦云。当然,从思想感情上,董对南宗一系绘画的亲近是很显然的,但并不能就认定其对北宗的贬抑,“五百年而有仇实父"这是何等的推崇!  李昭道 《明皇幸蜀图》55.9 x 81cm 绢本青绿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啟辰:二位老师说得很有见地,只是董的理论貌似总有“护短”之嫌,因为任何理论,任何讨论,如果设置之初,早已先入为主的稳座本方立场,难免有为得鱼而缘之感,我的意思是说,董实际上难免放大了自己所擅的阴柔、韵致一脉,同时又将刚健与苍劲人为的摒除和弱化。 如果说,是四两拨千斤的以柔克刚,那么在实操层面尚且客观,但董的观点感觉总有对北宗表面化的倾向。 以当下而言,董其昌这个南北宗论是否还对应得上,对于艺术评判还有意义么?  赵伯驹 宋代 《九成宫图》66 × 36cm 镜心 绢本设色 杨惠东:“文则南,硬则北。”所以,刚强,正是北宗的“原罪"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强调以柔克刚,老子说“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",水为天下至柔,而能水滴石穿,我们的武侠小说叙事中,大凡刚劲威猛的外家高手往往是送人头的角色,绝顶高手大多文质彬彬,看似弱不禁风而能绵里藏针。真力内敛,不动则已,动则一击必杀。 这就是以柔克刚,我们的传统文化,正推重这一点。南与北的分野,无关乎地域,"但其人非南北也”,而在于柔弱与刚强,由此推而广之,所有深沉、婉约、内敛、含蓄,皆可归于“南”至如慵慨,豪迈,张扬、外露,自然属于"北"。而在审美境界上,似乎无形中也就有了高下之别。  王维 唐代《雪溪图》36.6 × 30cm 绢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啟辰:我理解的笔墨也如杨兄所言,婉约含蓄中,不断渗化出内在的力量,是内化而不是外显的,所以具备更为充盈和持久的张力,这种张力其实和粗笔细笔是无关的,最主要是内在的,含蓄的,不断延展和化育出的生息之力。  王维 唐代《江干雪霁图卷》28.4 x 171.5cm日本京都小川家族藏 丁亚雷:作为一种价值评判,实际上南北宗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智慧生成机制的判断。作为形之于态的意识,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理心学说在绘画理论上的反映。董其昌受王阳明影响。王阳明从理学向心学的格致观念转变(渐顿之悟是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深化),可以看作是南北宗的直接基础。 有趣的是,也就是在这一时期,西方也在经历一种知识生成机制的认知转变。某种程度上说,两种转变的方向正好相反。这种相反在其后五百年的结果,也包括绘画发展的结果中得到了证实。 实际上,需要注意的是,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基础都应该是当下。画史画论问题也应该是这样。 今天的问题是,在经过20世纪以来,特别是康、陈、徐等为代表的对南宗绘画的重新审视后,今天其实又到了一个新的视野平台。谈论中国画问题,其实并不是谈论中国画本身,而是谈论其背后所代表的一种文化模式,或者说是一种对文化的认知变化。 旧话重提不在于旧话本身。中国画,也包括西方绘画的背后,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生成机制。我觉得文化生成机制是一个任何时代和历史条件下都面对的问题,文化生成机制应该是一个动态的问题。 旧的南北宗的语境早已经变了。但文化生成的问题一直都是新的问题。
 巨然 五代 《秋山问道图》156.2 x 77.2cm 绢本水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啟辰:语境确实变化极大,实际在当下的节奏,是有适合南宗的土壤的,私以为,南宗不拘泥于下苦功夫,很多的才情顿悟与综合修养会自然流露于笔端,灵气高的人很快就可以有一个相当的境界,时间不多耗在笨功夫上,以直抒胸臆取代频繁的打磨与试错,同时创做起来也相对自如畅快。但是于北宗而言,时间和精力是必须付出的成本,估计当代的语境下很难实现,大环境大背景都不容易支持,所以南宗更易得到大家的追捧吧。  李成《晴峦萧寺图》绢本设色,111.4cm × 56cm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 杨惠东:南北宗论在当时的影响固不待言,但就在董其昌之后不久,反对、质疑之声即出现,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,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高潮时代,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被定为一尊。董其昌以禅喻画,事实上他也并未能参透南宗禅中“法自我立”要义。所以石涛就说“今问南北宗,我宗耶?宗我耶?一时捧腹曰,我自用我法。” 王石谷是董的再传弟子,被推为“画圣”但他并没有为南北宗论所囿,后人谓:“画有南北二宗,至石谷合而为一。”因此,真正的高手,一如令狐冲的独孤九剑,以无招胜有招,一旦胸中存宗派、招法之念,已落下乘。后世庸才,贵耳贱目,随波逐流,崇南而贬北,正是画学衰微之因,无怪乎康有为说:“国朝近世之画,衰败极矣。 而且,值得注意的是,上世纪初,立场不同的康、陈、徐诸家,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画衰败之因归罪于南宗一系,并寄望于北宗画的精谨工细与写实,典型者当推徐悲鸿对仇英的极力推崇。民国时期,首先是从京津画坛始,出现了一股复兴北宗的小热潮,如作为当时的画坛领袖金城的实践,再如陈少梅的努力。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,所有的传统皆在怀疑和重新思考之列,甚至包括孔夫子。在唯新是尚的20世纪乃至当下画坛,古今之辨、雅俗之辨甚至华夷之辨,根本就已不成为问题,更何况南北之辨!所以在当下,我们谈南北宗,更多地是注重其审美境界之别而无关乎价值判断。  董其昌《仿赵孟頫秋山图轴》纸本设色,107.1×46.4cm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丁亚雷:前两天,很多人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段许知远采访许倬云的视频。应该是出于对许倬云话的认同才转的吧。许的谈话中有一个大致的话题,说是在文化生成阶段,许多看似形而上的问题,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,但却决定了后来人类文化的发展走向。人类文化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注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。这些问题的提出,原本不是为了获得非此即彼的答案。对这些“元问题”的思考、注解,成就了后来的文化史。 中国画南北宗的问题,应该也差不多。今天看,是不是可以把它算作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史的一个元问题? 崇南抑北原本是与笔墨有关的绘画品评问题,除了禅宗,除了理心,其背后是否有某种其它的文化心理因素?比如宋元之后文人对北方这个概念的一种微妙的情绪。似乎魏晋之后,“北方”在中国的概念就变得复杂起来。这也是中国画发展的重要时段,也包括画理、画论。  董源《寒林重汀图》绢本设色,181.5×116.5cm现藏于日本黑川文学院 杨惠东:橘生淮南则为橘,橘生淮北则为枳。一地有一地之地气,也必有一地之人文,以中国之大,地域文化之别随之出焉。这种区别在世俗生活中和文化精神上皆有明确体现。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在黄河流域的北方,之后出于多种原因,文化中心逐步南移,所谓的晋室东渡其实是南渡。那么,南渡的那批精英们对北方的态度自然是复杂的,一方面有河山之异的悲凉,另一方面,所谓南渡又曰衣冠南渡,象征着道统的南移,那么,当他们隔江北望之时,其眼神透露出的,除却悲凉之外,可以肯定,居高临下的傲然是必然的。 所以。“南"与"北"永远是一个有趣的话题,长期的发展中,分别已有了约定俗成的语义指向,形容一个人南人北相当然是褒义词,但如果说北人南相,则肯定不是一句好话,论英雄豪杰必曰燕赵,必曰齐鲁,但另一方面,论及文化,则必以江南为高,故曰江南才子。有些时候,南北是一种并列的关系,并无高下之别,如武术中的南拳北腿,又如词家以辛弃疾为北派,姜白石为南派。但大多数情况下,特别是元以后,文论、画论牵涉到南北,其高下轩轾自见。 还是回到南北宗,前面已经说过,董其昌并没有旗帜鲜明地崇南抑北,但其理论本身的混乱之处也不少,我一直都不太理解,为什么笔墨粗豪劲健的北宗山水会发源于水软山明的杭州,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社会学解释实在是有点扯!  董其昌《仿梅道人山水图》轴绢本水墨,07.35×38cm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|